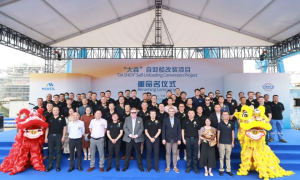2018年1月6日20時許,巴拿馬籍油輪“桑吉”輪與中國香港籍散貨船“長峰水晶”輪在長江口以東約160海里處發生碰撞,導致“桑吉”輪全船失火。經確認,1月14日16時45分,“桑吉”輪已經沉沒,船舶溢出的油仍在沉沒海域燃燒。

為何在大洋上發生碰撞?世界大洋航路相對固定且有業界普遍遵守的《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作為船舶規避碰撞的行動指南。公眾普遍認為海洋寬廣浩瀚發生船舶碰撞事故似乎幾率很小。航海實踐中開航前二副根據《世界大洋航路》、海圖資料綜合水文氣象等進行航線設計并由船長進行審核,遠洋航路往往多采用推薦航線,因此航路相對固定且來往船舶眾多,故保持駕駛臺值班瞭望是非常重要的。本次碰撞事故中“桑吉”輪從伊朗向韓國行駛,其在東海海域大致航向是由南向北;“長峰水晶”輪從美國向中國廣東行駛,其在東海海域大致航向是由北向南;同時,東海海域漁業發達,因此航道情況非常復雜故而航路相對較為擁擠。推測兩船由于航線設計原因在相遇時是對遇或交叉相遇,故而應當根據《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在通過雷達、目視觀察后進行甚高頻通話(VHF)溝通,并按照《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互相采取行動以保持清空。筆者注意到碰撞事故時間節點為20時許,遠洋船舶值班20時為大副向三副交班時,因此可能存在駕駛臺交接不清楚的人為疏忽因素。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作為船舶避碰輔助儀器在當代航海中愈發重要,也引發了對海員職業素養的擔憂。
有報道稱,“桑吉”輪的AIS自事發前24小時在臺灣附近海域提交信息后就沒有再提交過任何信息。因此有人猜測導致此次碰撞事故的原因或為有人故意關閉AIS,或因信號差,抑或是AIS出現故障。
AIS是誕生于20 世紀90 年代的一種新型航海儀器,集全球定位系統(GPS)、現代通信技術和計算器技術等多門類高新技術于一體。AIS在無需人工介入的情況下,可主動連續地向周圍船舶廣播包括船名、MMSI、船舶概況(類型、船長、船寬、吃水等)、船位、航速、航向和航行狀態等信息,也能接收來自安裝AIS 船舶廣播的上述信息。運用AIS可在屏幕上得到本船附近船舶的最近會遇距離(DCPA)和到達最近會遇點的時間(TCPA)等相關信息,這樣就能正確地識別對方船舶,判斷是否存在碰撞危險。如存在碰撞危險,可根據AIS讀出的船名、呼號,有的放矢地用VHF呼叫,進行有關航行安全的信息交流。由此可見,正確運用AIS對防止船舶碰撞,尤其是在能見度不良的水域避免船舶碰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船舶都安裝AIS,因此航海中不能單純依賴AIS,要充分利用雷達、電子海圖和VHF等航海儀器,包括目測瞭望,才能保證船舶航行的安全和避免碰撞的發生。
由于很多企業利用AIS跟蹤全球的石油運動軌跡,以便提前獲得可用于指導交易的各種數據包括石油輸出國組織主要石油出口國的發貨數據。因此,“桑吉”輪存在關閉船上AIS應答器的可能性(當然,也不排除東海海域由于系統故障及技術原因經常出現的AIS信號丟失情況)。在伊朗出口受到制裁限制時,伊朗船舶有時會試圖隱藏其運動軌跡。過去兩年,伊核協議解除了對伊朗石油的限制,但船舶關閉AIS應答器的事件仍時有發生。近期,美國可能重新實施制裁言論甚囂塵上,伊朗有更大可能性關閉其油輪的AIS。
關閉AIS以避免被追蹤的做法并不限于國有石油企業,一些全球最大石油交易者也在這樣做。特別是在伊拉克,因為庫爾德獨立而備受關注的庫爾德原油在土耳其地中海港口杰伊漢裝運后往往主動關閉AIS應答器以免泄露行蹤惹惱伊拉克聯邦政府。
何方為碰撞事故責任人?2018年1月25日,中國、伊朗、巴拿馬、中國香港特區海事主管機關共同簽署了聯合開展“桑吉”輪和“長峰水晶”輪碰撞事故安全調查協議。事故調查工作將在協議框架下,由四方聯合組成的調查組組織開展。
從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桑吉”輪隸屬于伊朗光輝海運有限公司并由伊朗國家油輪公司經營管理。此前在多篇報道中出現的租家韓華道達爾石化公司(韓華道達爾)應當是作為航次租船下的租家,以光船承租人身份出現幾率為零。通過美國對伊朗制裁歷史,可以很清楚了解伊朗國家油輪公司是伊朗石油外運主力甚至唯一承運人,特別是在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6國就限制伊朗發展核武及解除對伊朗的制裁問題達成協議前,歐美制裁對伊朗石油外運可謂招招致命。
自2012年7月1日起,歐盟全面禁止其成員國從伊朗進口石油,歐盟成員國的保險公司將不能為伊朗的石油運輸業務提供第三方責任保險和環境責任保險。目前世界各國運營油輪的約90%都是由國際保賠協會(P&ICLUB)集團承保。沒有了保險和再保險的支持,油輪無法出航。其原因,一是基于風險過大的考慮;二是在不能出示保險和再保險證明的情形下,絕大多數港口都不會允許油輪掛靠。
按照歐盟委員會決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將終止被歐盟制裁的伊朗銀行通過其網上交易系統實施跨境匯兌。SWIFT在國際金融服務市場占有壟斷地位,各國主要銀行均已加入SWIFT;石油基本上均用美元計價,沒有SWIFT的支持,貿易很難進行,在發生溢油事故時,賠償也非常困難。美國政府**法案,規定船舶在靠泊美國港口前,其所有人、承租人、經營者或船長需證明在此前的180天內該船舶未曾進入伊朗、朝鮮和敘利亞的任何港口。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第一貿易大國,其港口也就自然成為全球各主要貨運企業無法避免的靠泊地。美國海軍控制著全球16條主要海上通道,世界各主要油運企業油輪的動向均在其掌控之中。作為一個全球性行業,航運企業無法選擇伊朗而放棄美國。
2012年8月10日,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簽署相關法律,規定對任何向伊朗出售、出租或提供油輪以及為伊朗國家油輪公司提供保險業務的企業和個人實施制裁。伊朗尚可依賴本國的油輪向外出口原油,但是缺乏制造油輪的能力,禁止向伊朗出售、出租或提供油輪,則從根本上限制了伊朗出口能力的提升。2016年8月開始,規模龐大的伊朗國家油輪公司正在逐步重返保賠協會,結束了多年來因制裁無法獲得保險的窘境。此舉解決了過去7年來伊朗船舶無法獲得船舶保險的問題,并使得伊朗國家油輪公司油輪船隊能夠在此前不接受伊朗船舶進入的港口恢復運輸貿易。
“桑吉”輪所在的保賠協會SteamshipMutual將成為后續事故處理主要參與方,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否則沒有保賠協會兜底的“桑吉”輪后續賠償將面臨極大問題。
如何進行溢油損害賠償?伊朗伊斯蘭共和通訊社IRNA援引伊朗港口和海事組織數據稱,“桑吉”輪上載有11.35萬噸凝析油、1956噸重油以及118噸柴油。
截至2018年1月22日,現場累計出動海事執法船、專業救助船、海警船、清污船等共計71艘次開展清污工作,累計清污面積107.2平方海里。預計將產生高額清污費用及后續環境漁業相關利益方索賠。
為了解決油輪貨油和空載油輪燃油污染損害賠償問題,國際海事組織(IMO)組織制訂了CLC92和《1971年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公約1992年議定書》(FUND92)。CLC92規定船舶所有人在油污損害賠償上的責任限額(船舶所有人一般通過購買P&ICLUB保險,獲得該責任限額下的保障);而FUND92通過向締約國石油進口商攤款設立的國際油污基金,在船東責任限額之上,對賠償不足的部分予以補充。1980年中國接受《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CLC69);1999年又接受CLC92和FUND92(僅限于中國香港),CLC92于2000年1月5日對中國全部生效,中國國際航行船舶均已執行國際公約的規定。伊朗分別于2008年和2009年接受CLC92和FUND92。為了解決非油輪和載貨油輪燃油污染損害賠償問題,IMO于2001年3月通過《國際船舶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燃油公約》),通過對非油輪船舶強制油污保險的辦法解決了非油輪污染損害賠償問題。《燃油公約》于2008年11月21日生效,中國和伊朗均為簽約國。
在基本解決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問題的基礎上,為了解決船舶運輸有害有毒物質污染損害賠償問題,IMO于1996年通過《1996年國際海上運輸有害有毒物質的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HNS公約》),但是目前尚未對中國生效。國際上建立船舶有害有毒物質污染損害賠償機制的思路與油污損害賠償機制的思路大體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油污損害賠償責任是通過CLC92和FUND92兩個公約共同構成一套完整的賠償機制,按照船東和石油貨主共同承擔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原則,建立了一套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機制。一旦船舶發生油污事故,首先由船東或其船舶保險人在CLC92規定的船東責任限制內賠償,超過船東責任限制的損害再根據FUND92公約規定的責任限制進行補充賠償。而《HNS公約》則把船東和貨主的責任通過一個公約確定了下來。
在上述三個公約體系框架下,國際上就基本解決了船舶泄露油類物質或有毒有害物質造成污染事故時的賠償問題。
盡管中國相關部門將凝析油列為原油類產品,但是“桑吉”輪所裝載的伊朗南帕斯凝析油在伊朗歸于成品油序列管理的,該油品并非原油類的持久性重質稠油而是揮發性極高的天然氣氣田開采時凝析出來的液相組分。
由于CLC92和FUND92兩個公約對油類適用的范圍是:“油類”系指任何持久性烴類礦物油,如原油、燃料油、重柴油和潤滑油,不論是在船上作為貨物運輸還是作為這類船舶的燃料均屬于此類。
因此,“桑吉”輪所裝載的凝析油所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可能無法適用CLC92和FUND92兩個公約共同構成的完整賠償機制;“桑吉”輪所裝載的作為船舶燃料的1956噸重油,以及118噸柴油有望適用《燃油公約》。
來源:航運交易公報 張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