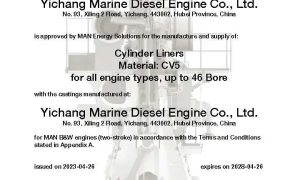一個只讀過三年私塾的窮家少年,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成長為新興機器行業的一代巨子;他并沒受過嚴格的科班訓練,卻在內燃柴油機剛在全球市場露頭之際,就沒日沒夜認真琢磨這個新生事物,為此甚至玩出了潛伏洋船,偷偷把人家的發動機“大卸八塊”,細細分解研究的“諜戰”戲碼,最終制成了國產柴油機,并推動了華南航運業的技術變革。這個故事如此勵志,它的主角又是誰呢?
英軍船塢大開眼
進入“奇幻新世界”
今天,當人們談起站在新技術潮流之巔的“新貴”們,總難免要說一說他們輟學創業的經歷,比爾蓋茨輟過學,喬布斯輟過學,馬云雖然沒輟學,但也只是讀了個師范學院,不是什么名牌大學。
提起100多年前推動航運業技術變革的工商業大鱷薛廣森,現在的人們當然已經相當陌生了,但他“輟學創業”的經歷,卻遠比以上各位“大佬”更傳奇。
船塢當學徒
用心學本事

1865年,薛廣森出生于順德龍江鎮一個蠶桑佃農之家,因為家里窮,小時候只讀了3年私塾,就輟學了。17歲那一年,他父母雙亡,只好跟著親戚,去到香港討生活。接著,他進了英軍在香港的一個船塢當學徒,一干就是多年。
如果換了一般人,滿身油污地辛勞一整天,無非就是為了混個肚兒圓,不大可能有心從現有的環境里尋找更多的機會。薛廣森的心智卻要敏銳得多,他仿佛進入了一個由機器構成的“奇幻新世界”,一天24小時用來摸索這個新世界的門道,都嫌不夠用。轟鳴的馬達在他聽來一定是悅耳的音樂,一個個精密銜接的構件也一定讓他驚嘆于人類頭腦的力量。在這個“奇幻新世界”里沉浸得越久,他內心也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這些威力無窮的機器,可以給貧窮的家鄉帶去什么樣的改變。
穩扎穩打
終成商業巨子
1895年,薛廣森回到順德,在順德一家繅絲廠擔任機器總管,由于工作出色,被當地一個大絲商慧眼看中,力邀他合作。1898年,他拿著自梳女胞姐資助的250銀圓,與這個大絲商一起在大良辦了一個機器廠,同時出任經理。當然,這么一點錢,只能讓他做個小股東。苦心經營七八年后,他才有了“單飛”的本錢,招股自辦了一家規模相當的機器廠。

1911年,他又與當時在業內已頗有名望的陳拔廷、陳沛霖、陳德浩等人在芳村大涌口辦起了協同和機器廠(即廣州柴油機廠的前身)。
在此后的數十年間,協同和逐漸成為華南最大的機器廠,只有3年私塾學歷、從一個小學徒起步的薛廣森也一舉成為名震全國的商業巨子。
“潛伏”英國油輪
偷師柴油機門道
薛廣森從輟學少年成長為商業巨子的經歷,我們短短幾行字就說完了,但若要仔細探查其間甘苦,那一定會寫成一本厚厚的大部頭。不過,用一句民間的俗話來說,“只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打”,向來是人性。與薛廣森同時代的人,大多也只用“運氣好”來解釋他的成功,對此,薛廣森也只能淡淡地回應一句:“運氣再好,還得靠自己有學識,有本事才能利用它,否則運氣來了,你還不知道呢。”
為學珠算 不惜伺候人
學識和本事當然不是白來的,而是要付出遠遠超乎常人的努力。薛廣森到底有多勤奮呢?第56輯《廣州文史資料》刊登的《薛廣森和他興辦的實業》一文講了一個小故事:當年薛廣森還在順德那家繅絲廠做經理的時候,廠里有位“更夫”精通珠算,這位“更夫”有抽***的嗜好,薛廣森本來特別討厭***,但為了這門功夫學到手,他恭恭敬敬請那人抽***,還耐著性子為他擦拭煙具,等此人過足了癮,再向他虛心求教。而協同和工廠開辦之初,只有兩三間茅屋,一到晚上,只能靠伙計手里蠟燭的微弱亮光,細細研制和打磨機器。可見,勤奮固然不能保證一個人成功,但如果一個人連必要的勤奮都做不到,卻還要感慨自己為什么不能揚名立萬,就真有點扯淡了。
柴油機問世 被他盯上
協同和機器廠研制了一些新型機器后,經營漸漸上了正軌。接著,薛廣森和其同仁又把眼光投向了在世界市場上剛嶄露頭角的內燃柴油機。
我那一點可憐的歷史知識并沒完全還給中學老師,還記得蒸汽機是在18世紀中葉由瓦特發明的,而柴油機則直到1892年才由德國工程師制成。在薛廣森和其同仁盯上柴油機時,國內沒幾個人聽說過它呢,那時省內外近百條航線數千艘船舶,用的都是外燃蒸汽機,每條船都要裝個笨重的大鍋爐,不但使得船舶吃水深,還特占地方,而且燒煤炭也比燒柴油貴得多。薛廣森及其同仁決意仿制柴油機,推動一場技術革命。
苦干一年 仿制柴油機
仿制柴油機,推動技術革命,聽起來相當勵志。問題在于,這個剛在全球市場上露頭的新玩意到底長什么樣,大家都還不知道呢,要想進口一臺來研習,又花不起這個錢。
就在大家發愁的時候,1913年的一天,英國亞細亞公司的一艘油輪停在了大涌口附近,托他們檢修。這艘油輪恰巧安裝了一臺內燃柴油機,真是天賜良機,薛廣森及其同仁就借著上船檢修機器的機會,一點點摸清柴油機的門道。
船上的華人輪機長被他們的熱情感動,多次暗中相助,之后更借口“大修”,讓他們把發動機“大卸八塊”,搬回廠內,細細分解與繪圖。他們把這臺柴油機當成寶貝一樣琢磨了幾個月,獲得了詳細的技術資料后,才完璧歸趙。
就這樣,薛廣森和“三陳”靠著多年自學來的機器知識,又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終于造出了一臺像模像樣的柴油發動機。其間,他們經歷了多少次失敗,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自辦航運
倒逼變革
造出柴油機的高興勁還沒過去,薛廣森及其同仁又碰上了新的難題:這些先進的機器壓根賣不出去。在廣州幾十家航運公司的老板們看來,蒸汽鍋爐燒得好好的,干嗎要花一大筆錢進行技術改造?再說,這個洋玩意剛問世,誰敢保證一定好用?就這樣,薛廣森及其同仁制造出來的柴油機居然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沒幾個人看得上。大家想來想去,唯有自辦航運公司,才能推廣新技術。
白菜價買舊船 裝柴油機
幸而,那時的薛廣森除了協同和機器廠外,又自辦了十來家新興的碾米機器廠,俗稱“十大米機”。辦個航運公司,貨源不用愁,又可以推廣新技術。于是,1918年,粵海航運公司在廣州仁濟路一棟小樓里成立了,其名下的10艘船舶,原本都已毀損嚴重,其他船商不要了,用白菜價賣給了他們。薛廣森及其同仁精心修理,整飾一新,又換上先進的內燃柴油機,頓時“鳥槍換炮”,煥然一新,稱為電船。
“粵海航運”的運營成本,要遠遠低于固守蒸汽鍋爐的各大航商,同樣是在廣州和清遠之間走一趟,用煤炭燒鍋爐的機動船,成本是120塊銀圓,燒柴油,卻只需30銀圓。
被罵“十大害” 最終贏了

粵海公司的十艘電船一出航,就攪得整個航運業不得安寧,其他航商看著客源人紛紛被“粵海”吸引過去,破口大罵其是“十大害”。雙方的價格戰愈演愈烈,給客人送米送油送演出票等優惠措施也拼得越來越沒底線。據業內人士回憶,這一場“戰爭”之激烈,之后在廣州航運史上再沒出現過。不過,懸殊的成本放在那兒呢,老航商們支撐了沒幾年,就俯首求和,紛紛購買協同和開發的柴油機,換掉笨拙的鍋爐。激烈商戰告一段落,一場技術革命拉開序幕。如果你要問,薛廣森為何能讓原來看不起他的老牌航商沒幾年就俯首求和,從而推動了這場變革,答案也只有一句——“走自己的路,用事實說話。”
(注: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第56輯《廣州文史資料》。)
來源:廣州日報